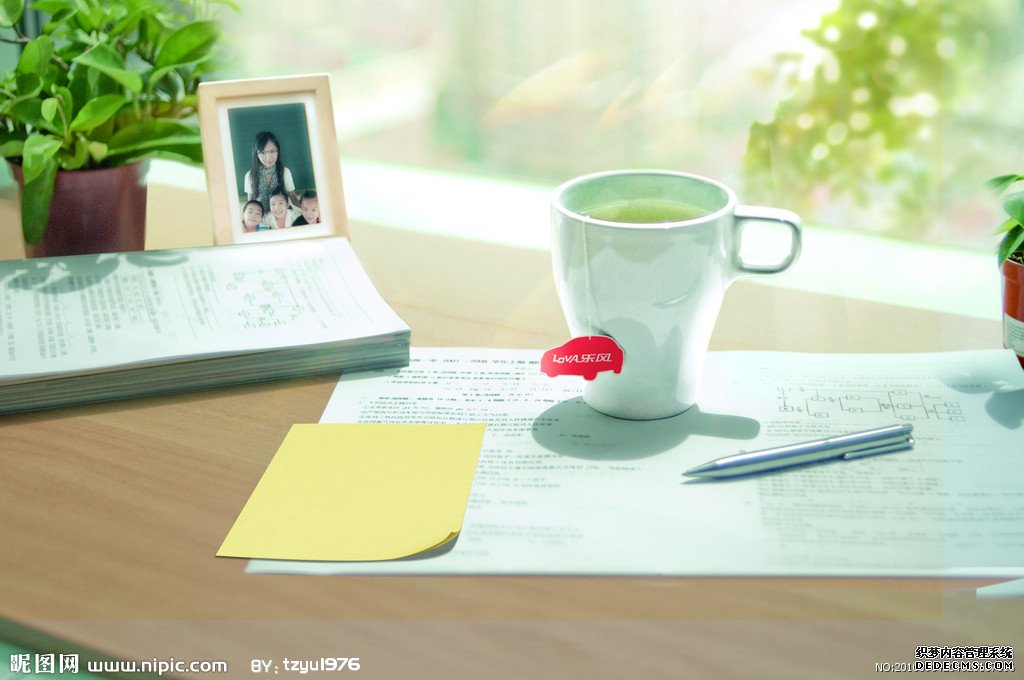 天高云淡的九月,令人心往神驰;九月的丹桂飘香,最醉人心。 九月犹如一壶浊酒,忍不住想要尝一尝。 九月令人念旧,念想的潮水掀起情感的波澜,涨潮决堤。 九月记忆是我刻骨铭心的怀想。 欢笑刻在石头上 看着莘莘学子入学时的兴高采烈,一下子激起我回想自己做学生的那一段段青涩。每到9月的第一天,我们都喜气洋洋,满是领新书时那一瞬间的喜悦,满怀对新学年的希冀,满腔藏着同学们许久不见的心里话。九月是孩子们破茧成蝶的季节,一天一个样,日渐走向成熟和辉煌。 少年时代的趣事,就像刻画在石头上一样,风雨洗不尽,岁月抹不掉,珍藏到永久。念三年级的同桌--“大吃一斤”,是同学们课余生活的“开心果”,每个同学回忆起他,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一次作文课上,新来的老师一脸疑惑连叫三声“姚-禾-斗”,却无人应答,大家肚子里也是一连串问号。一向活跃的课堂顿时变调了。好在“危难出英雄”,副班长“小机灵”周爱国这时赶紧出招,向姚科使劲地使眼色,原本聪明的姚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时粗心大意,把姚科写成“姚-禾-斗”,胆战心惊的他向老师怯怯地要回了作业本,随之而来的是满堂大笑,老师竟也未能免俗,露出了甜甜的笑容,课堂顿时成了欢笑的海洋。快下课前,老师例行检查作业,姚科的作文又闹了一个大笑话。他在作文里写道:“上学路上我一路奔跑,一不小心,踩了一坨牛屎,大吃一斤。”老师在班上作为案例讲述时,说该同学“一”字用的好,但“斤”字用的更“妙”,同学们又在哄堂大笑中奔向欢乐的操场。从那以后,“大吃一斤”就成了姚科的外号,至今还有人念念不忘;也是从那以后,姚科痛改“前非”,变粗心为专心,学业成绩扶摇直上,现已是一大型公司的经理,事业上把一大群学友甩得远远的。 1989年对边远山里人来说,是个信息闭塞、生活条件艰苦、媒体资源贫乏的年代,但那年的“六一”无疑是精彩纷呈的,永远烙印在同学和乡亲们的心间,至今回味无穷。那年的“六一”文艺汇演是王春林、刘梅初等老师精心筹划导演的,有气势不凡的歌伴舞、有惟妙惟肖的人物小品、有欢快的竹笛声、有悠扬的二胡独奏、有让人捧腹大笑的相声,有节奏感特强的快板,特别是一个城里女孩带给大家的一首《黄土高坡》,声情并茂地演唱,别样的风格犹如清风拂面让人耳目一新,底下掌声四起,把汇演推向了高潮。那个已经遥远的儿童节是那代人精神文化上的大餐,是生命中的盛典,让人们一饱眼福,让同学们为此事喋喋不休说到了放暑假。 永不疲倦的教师梦 那些永远奉献永不索取永不疲倦的老师,他们传授了我们知识,锻造了我们胆识,开阔了我们见识,让我在这浓情四溢的九月永远是温存,永远是感激,永远是怀念。廖永健,乡村代课教师,朴实敦厚,典型的山里汉子。他有太多的事迹可以让那一方人永远记住他,为了18个学生能顺利上学读书,他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住在学校里,苦苦地支撑着几个村唯一的小学。作为一个极贫困偏远山区的民办教师,他的工资不仅少得可怜,而且被长年被拖欠,他甚至连家都没成。每年涨山洪的季节,他都要亲自去断桥边接送学生,在危险地段,他更是背着学生趟过河水。他的事迹在当地人中津津乐道,可除了得到一点虚名外,对于他,对于他的学校,没有带来丝毫的改变。直到暴发那场最大的洪流。那一次,廖永健在生死边缘走了无数次,救下了25名学生,却终有一个孩子被洪水吞噬了生命。他自责自怨,无法面对那如花的生命在面前殒落。他觉得对不起教师这个崇高称号,他连一个孩子稚嫩的生命都保护不了。那次灾难之后,他便放弃了教师的职业,成了无数普通山里人的一员。后来带着一家人在外卖小菜,生意还不错,就在去年的暑假里一天清晨,去市场卖菜,被车无情的撞了,一撞就不再回来了。可惜英年早逝,留给孩子们一直是痛心,一直是留恋,一直是叹息。 十年前的九月,做了17年学生的我,来到了我毕业的中学做了一名“先生”,有初为人师的喜悦、惶恐、期盼和重任在肩,真是五味俱全,难以言尽。那个九月,我紧张我忙碌我快乐!紧张我的教育教学经验不足;忙碌新学期的各项工作;快乐我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 人生的第一次总让人无法释怀。分下来的第一个期末考试,学校安排我出初一语文和初二地理试卷,还要油印试卷。当时教学设施设备简陋,出试卷还好说,印试卷我头“大”了。我赶紧收集相关资料,找来蜡纸、钢板和刻字笔,独自苦苦“奋斗”六个小时,样卷搞定了。油印试卷是项新工作,我一筹莫展,硬着头皮开始新的“万里长征”。刚开头不错,280张试卷线条清晰,色泽分明,我不禁沾沾自喜。到印第二套试卷时,一不小心,蜡纸破了,只有重新再刻,到凌晨2点多才忙完。当时困极了,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第二天早上,简单洗漱后,去食堂吃早餐的路上,从来没有“回头率”和“收视率”的我得到了全校师生的青睐,我总感觉“不对乎”,原来是我脸上有几块油墨印记未清洗干净。 从教的日子里,最深刻还是课余创办“雨石”文学社的那段辛酸与欣喜的日子。长夜里,孤灯下,几个学友,一群学子,凭着对文学的执着和追求,我们相约“宇石寨”,创办“雨石社”,寻觅“雨石梦”。国繁老师和我一起推敲社名、制定章程,一起带同学们到“宇石寨”采风,一起约稿征文、审稿改稿,一起联系印刷厂,一起在寒风凛冽的早晨等候公共汽车,一起邀请名师搞文学讲座、一起赴“孔孟之乡”--曲阜参加文学论坛。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篇学生文稿,多少回曲曲折折,我们“雨石人”在“痛苦”中砥砺前行。天道总酬志坚人,我们的学生在各级作文大赛上捧回的奖杯奖牌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我们的文学社获得全国示范文学社就是最好的慰藉。 怀念留在记忆里 一个人的经历也许是一曲悠扬婉转的民族小调,也许是一道美丽独特的风景,也许是一杯难以下咽的苦药,或许还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已经离开三尺讲台的我,校园的那些年、那些人和那些事,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昔;却永遥不可及。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触及至此,时而纠结,时而甜蜜,时而思念,时而放不下,留在记忆的长河里只有怀念只剩怀念。 怀念那些渐渐长大的孩子们。 怀念那些与我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的同事们。 怀念那那简陋但始终充满欢歌笑语的校园。 怀念生命中那些最有价值最灿烂的九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