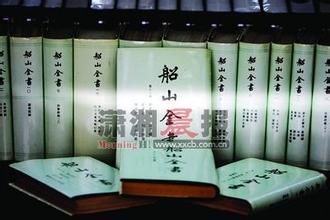
岳麓书社印行的船山全书张学智先生在《明代哲学史》当中针对王夫之“乾坤并建”的哲学命题,做过一个发挥。他把王夫之的“乾坤并建”命题发挥为:乾代表人的精神的方面,物的动能的方面。坤代表人的才能的方面,物的体质的方面。(张学智《明代哲学史》第三十一章)毫无疑问,这是张学智先生基于王夫之哲学整个体系的理解做出的个人解读。我在这里并不追究张学智先生的解读是不是完全贴切王夫之本人的哲学思考,我所需要的是对张学智先生的解读的再运用。 为了方面理解,我把张学智先生的解读再细化一下。 乾:人的精神的方面、物的动力的方面。定性为两个指标:1.人之精神。2.物的动力。 坤:人的才能的方面、物的体质的方面。定性为两个指标:3.人之才能。4.物之体质。 再把这四个指标具体适用到历史上的满清王朝,那么四个指标各自指向何处以及考察这四个指标的意义就是: 1、人之精神——满清王朝决意工业化的精神力、意志力。考察这个指标就是检验满清王朝的上层建筑有多大决意推行工业化。 2、物的动力——满清王朝推进工业化的物质动力。考察这个指标就是检验满清王朝的经济基础推进工业化,究竟能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变革动力。 3、人之才能——满清王朝作为一个政权推进工业化的能力。考察这个指标就是检验满清王朝的上层建筑推进工业化,究竟能爆发多大的执行力。 4、物之体质——满清王朝推进工业化的物质基础。考察这个指标就是检验满清王朝的经济基础的现状,与工业化的经济基础相差究竟多远。 四个指标细化出来了,我们就要看,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哪些指标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以及为何阻碍的缘由? 考虑满清王朝碰到工业革命的特殊情况,我们就先从“物”的两个指标开始解析。 首先是第4个指标——满清王朝的“物之体质”。 毋庸置疑,满清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农业国。但我们这里要谈的是,西方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也才刚刚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早,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算基本完成。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虽然工业革命开启的早,同样也是在南北内战过后,工业化的速度才开始加速。德国更迟,普鲁士直到19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统一以后才迅速深入。日本、沙俄更迟。所以是不是农业国,作为经济基础的现状都不能成为阻碍第一次工业革命推进的缘由。因为各主要列强没有完成工业化之前,同样也是农业国。而且即使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也因为地理过于遥远,并没有实力吃下整个中国。这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所证明的。 故,第4个指标不构成中国近代未能跟上西方步伐快速工业化的缘由。 第二,来看第2个指标——满清王朝的“物的动力”。考察这个指标,就得排除“人”方面的因素,只看满清王朝的经济基础一旦全力推进工业化,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推进工业化究竟能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因而这个指标必须得考量农业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以及与科学技术相应的人才差距,还有就是国家的财政税收。 先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发明: 1712年 英国人汤姆斯·纽可门获得了稍加改进的蒸汽机的专利权 1733年 凯伊·约翰飞梭 1765年 詹姆士·哈格里夫斯珍妮纺纱机 1769年 阿克莱特水力纺机 1769年 瓦特改良蒸汽机 1778年 约瑟夫·勃拉姆抽水马桶 1779年 克伦普敦走锤纺骡 1785年 卡特莱特动力织机 1796年 塞尼菲尔德平版印刷术 1797年 亨利·莫兹莱螺丝切削机床 1802年 詹姆斯·瓦特改进了牛考门蒸汽机,现代蒸汽机成型 1807年 富尔顿蒸汽轮船 1812年 特列维雪克科尔尼锅炉 1814年 史蒂芬孙蒸汽机车 1815年 汉·戴维矿工灯 1844年 威廉·费阿柏恩兰开夏锅炉 从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只要愿意学习,一个技术工人完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把这些技术学透、吃透。而这也是有史实作为支撑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讲述日本明治时代的视频,其中讲到日本明治时代的纺织业发展。涩泽荣一有意建立日本本土的纺织业,但苦于没有技术和人才,于是找到一位在英国留学的留学生。那位矮小的日本留学生放弃学业,只身前往英国的纺织厂学习几个月时间,把英国当时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全部吃透,然后回国帮助涩泽荣一,在很短时间里就建立了日本本土的纺织业,让日本从纺织进口国变成纺织出口国。 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相对于农业国的科学技术差距并没有多大,农业国并不能构成阻碍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普及的因素。当然这其中还要提到资本的问题,但毋庸多言,明清两代中国几百年白银顺超,国内资本只可能积累非常高,但不可能少。 故,“物”方面的第2个指标同样也得排除,满清王朝作为农业国的经济基础,推进工业化的变革力量是足够的。 “物”的指标全部排除,我们就得来看“人”的两个指标。 第三,我们来看第1个指标,也即满清王朝的“人之精神”。这个不用多说,满清王朝在“人之精神”上边只有负面,绝无正面。 但在展开之前,我必须得多说一篇看似题外的话。在我们的国人脑海中,几乎形成一个共识的论调。儒家治国的意识形态保守,“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导致中国王朝封闭自守,让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中国因而落后。于是五四之流的论调上演,所谓儒教愚弄中国数千年,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所谓的文明,中国必须得彻底打倒儒家文明,中国才能进步。 因而,满清王朝在“人之精神”上边出现的问题并非满清王朝的原因,而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原因。是儒家意识形态愚弄了满清王朝,或者是满清这个有着强烈进取心的部族王朝中了汉人的毒。罪不在满清王朝,罪在儒家思想。 进而得出引申逻辑:即使不是满清王朝,只要还是儒家意识形态治国的汉人王朝,碰到工业化,中国也一样会僵化封闭保守,中国文明依旧没有出息,中国不可能会有什么前途。 然而史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这里还要谈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几位儒家士大夫当中的卓越思想者,我们来看他在“天”、“道”等核心命题上边是怎么说的? 先说“天”,儒家学说当中的“天”有多种意义,王夫之肯定了“自然之天”、“历史之天”,否定了“人格之天”。 先说自然之天,王夫之立足于气论,认为“天”是外在的自然世界,本质上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因为构成“天”的“气”是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气”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原话:“气无可容吾作为”,其他还有许多类似表述,不再一一引述,具体可以参见《张子正蒙注》)“天”从自然意义的角度来说,肯定不可能出现本质上的改变。这即儒家一脉相承的自然意义的“天”。 但在自然意义的“天”之外还有历史意义的“天”。王夫之对这个“天”给出了两个定义:“理势合一共成一天”,“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这里内容就多了,细看推荐张学智先生在《明代哲学史》第三十一章王夫之哲学的专门研究。我这里概括的说的话就是,人类社会在某一个阶段,肯定都会存在一些必须要实现的“理”,比如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人民的心智要提高,生活的水平要提高,不过事实上,这些“理”不一定就会实现,也即“势”不一定能够成就“理”。所以王夫之强调必须得理势合一,理势合一才能共成一天。而“天者,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者也”又为“理势合一共成一天”提供另一面的理论支撑,历史意义的“天”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随着历史推进不断发生变化的,需要人们去提纯,去总结,去升华,如此方能不断进步,进而实现“理势合一共成一天”。 如此,也就从根本的哲学命题上瓦解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与之相应就是王夫之的“道”,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词传上》中说:“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 概括的说,所谓“道”,人是不可能治的,形而上的东西,你脱离了“器”怎么治?你没法治。所以不能成“器”的东西,人也没法“治”。上帝意志你根本没法治,谁能把上帝意志治给我看?人只有通过治具体的“器”才能显道、成道。所以今人把王夫之的“道器”观抽象成为四个字:“治器显道”。君子不能“不器”(不考究这句话原意),君子必须得“器”。儒家的“道”也定然会因为“器”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变化。 由此,王夫之得出了自己的进步历史观:“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因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乐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周易外传) 站在历史的角度,毫无疑问,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道。古时的道只适合于古时,今天只能立足于今天的“器”治今天的“器”得今天的“道”,人类历史毋庸置疑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观也必须得是进步的、开放的,而不能是僵化的、顽固的。 废了这么大篇幅说王夫之的进步历史观,看似只是哲学,与满清沾不到边,其实大大不然。 近代以来,湖南的人文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各省,而人们又多把功绩归于曾国藩。但多不知,曾国藩等人受到王夫之哲学的影响极深极大。而且正是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王夫之哲学才能流行中国,对近代中国构成巨大影响。 因为王夫之本人鉴于满清开国时期“率兽食人”的禽兽行径,拒绝这个夷狄罪恶的部族王朝,坚守民族本位,常年隐于深山,许多学问成果一直未能在社会上形成影响。直到1839年才有一位姓邓的人少量刊印过非常不全的船山遗书,影响不大。到了曾国藩兄弟动用江苏省财政力量刊印《船山遗书》,方才让王夫之的学问为中国人熟知。更值得玩味的是,曾国藩成就的湘淮系是近代中国最先觉醒,最先提倡工业化的儒家士大夫群体。 所以总括的说,儒家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到了明清之际,已经进步到了王夫之这类鲜明进步历史观的高度理性水平,反而满清统治者不仅不用这些儒家思想,反而大兴文字狱、思想禁锢等种种措施,限制进步儒家思想的传播。直到太平天国重创满洲勋贵,满清王朝禁锢不住了,儒家进步的思想才能广为传播,即使如此,这些进步的儒家思想也从未成为过满清的治国政略。 试请问,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进步还是满清王朝的原因?是满清中了汉人的毒,还是满清毁了儒家思想? 如若中国近代王朝采纳王夫之这类鲜明进步历史观的儒家思想,中国还会封闭僵化保守吗?中国还会拒绝工业化吗?中国还会没有决意推进工业化吗? 说这么多,乃是不得不辨。纠正五四以来倒果为因、荒谬绝伦的思想遗毒。而且为后边第3个指标“人之才能”做理论铺垫。因为不能辨清是满清毁了儒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毒害满清,就无法理解第3个指标上边满清王朝的罪恶之处。 最后,第3个指标,满清王朝的“人之才能”。考察这个指标,就必须得先谈满清王朝的治国原则,政体架构。 满清自努尔哈赤、皇太极治政就开始强调旗人与非旗人的不同,关键核心职位只能依靠旗人,除了入关篡夺天下时期因为不得已重用一些汉人,其后在军事实权、财政实权、人事实权、地方实权等诸多方面,不是全部交予旗人,就是多依靠旗人。也即今人总结出来的“满洲本位制”。 结果就是,除入关篡夺天下时期,以及后期满洲勋贵败落时期,整个满清两百年上下,只有岳钟琪一人为汉人大将,而且此人下场悲惨,逼迫此人临死遗愿让后人入旗。为满清王朝兢兢业业几十年的李鸿章,到了东南互保结束,准备北上处理善后事宜之时,李鸿章在列强内部有国家有意改换满清王朝皇帝的背景下,与英国港英总督卜力秘密接触,试探英国有没有意向帮助当时的中国改换一个汉人皇帝?注意,曾经的康党李鸿章连光绪都在抛弃之列,为何他一定要试探英国会不会帮中国改立一个汉人皇帝? 说白了,满洲本位制,李鸿章比谁都要深刻了解。 满洲本位制在,他李鸿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满清王朝实质意义上的真宰相。即使西方鬼畜把他视为满清王朝事实上的“政府首脑”,访问沙俄,沙皇给予的礼遇让他受宠若惊,但他李鸿章心里十分清楚,他从来没有成为过满清王朝的“政府首脑”,他只是一个“裱糊匠”。 这产生了什么恶果? 李鸿章其人签署无数不平等条件,被人称之为罪人。但实质上,他的个人才能、他的个人抱负都是过得去的。可满洲本位制在,他成不了真宰相,所以他根本无法清退体制内的反对者。若是宋明两代这类中国王朝,李鸿章得到光绪这类有意变法的皇帝支持,成为真宰相,结果无非就是谁反对变法,就把谁清出体制。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再有能耐也只能窝在洛阳,只能看着王安石推进各项变法。当然,王安石、张居正这类都是因为打击特权阶层利益,最后人亡政息。然而工业化不同,工业化是做大蛋糕,前有王夫之这类儒家士大夫做理论论证,后有利益驱动,只要工业化进程开启,即使李鸿章死了,工业化的脚步也不会停。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官营的传统,真宰相们推进工业化,他们完全不必顾虑所谓中小地主的情绪,也不必顾虑特权阶层的意见。张居正极权之时,连书院都敢灭,还怕什么特权阶层?即使体制内外的人再不满,只要皇帝不点头,谁也推翻不了真宰相们的执政意志。真宰相们只需要通过各项政治手腕,排挤政敌,提拔亲贵,动用行政手段,把政府机构的执行力提升到极致。让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的经济主体,动用国家力量经营工商业。依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积累,只须给真宰相们十年时间,真宰相们就可以利用官营产业,让全天下人看到蒸汽机和火车的威力,感受到工商业带来的巨额经济利益。 其后的事情就不再是要不要搞工业化的事情,而是由谁来主导工业化的事情。因为特权阶层的分肥盛宴必定上演,官商勾结的财团不可避免出现。我们上一次上演特权阶层分享蛋糕盛宴的时间还不太远,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人不安分了,不断在鼓动搞新一轮的蛋糕分享。所以所谓中小地主没有经商的意愿,所谓超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工业化,都是站不住脚的。 利益的闸口一旦打开,谁也别想把这个闸口再关上。 谁阻挡这个进程,谁就得死。 历史上满清王朝的症结在于,李鸿章等人由于始终未能掌握中央实权,未能成为中国王朝正常应有的真宰相,导致洋务运动在理论上储备不足,实干上效率太低,影响太小,未能从根本上让特权阶层认识到工业化带来的巨额利益。 典型就是中国的铁路发展进程。 中国第一条小铁路——展览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沿着护城河修建了一条一里长“展览铁路”德小铁路,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一条铁路。不久,清统治者以:“观者骇怪”为由,勒令把它拆掉。 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淞沪铁路。1876年,上海怡和洋行英商在未征得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手段在上海擅筑,擅自修建了淞沪铁路(从吴凇到上海),于1876年7月建成通车,全长15公里,经营了一年多时间,这是中国最早办理客货运输业务的第一条铁路。后来清政府用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全部被清政府赎回拆除了。 中国人自修第一条的铁路——台湾基隆矿区铁路。1877年,洋务派大员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基隆煤矿的老寮坑矿地至滨海泊船处,自行修建台湾基隆矿区铁路,开创了我国自行修筑铁路先河。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1881年中国人建成自己修筑的另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运客的铁路——台湾基新铁路。刘铭传于1887年奏准修建台湾省铁路。 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开始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真正成功并保存下来加以实际应用的第一条铁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 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干——京张铁路(丰台柳村--张家口)。 中国第一条华侨出资兴办的铁路。是1905年修筑的潮(州)汕(头)铁路。 看上边满清王朝治下中国铁路的进程,如若是李鸿章决心搞洋务的儒家士大夫会出现赎回拆迁的大笑话?会几十年发展缓慢?相反,在1872年,因为沙俄侵占伊犁,李鸿章趁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当然,他不是真宰相,王夫之这类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未能深入人心,他的主张很快湮没无闻。等到福建水师完蛋,李鸿章得到满洲勋贵的个别人支持,他的腰杆子才硬了许多。结果呢?还是同样。不是真宰相,没有进步的儒家思想熏陶,一切休提。 而正是看到了满清王朝的巨大负面作用,让我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核心命题存在问题的缘由,即使加上一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不妥当。 经济基础只能起基础作用,以及限制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在人力可以实现的范围内,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不是反过来。 因为物的两个指标——第2个指标和第4个指标,只能推动人力在一定历史阶段内必须得从事某项进步事业,但又让人力的行为无法超出一定限制,不可能任由人想做到什么程度就能做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两个指标严格说,排除人的两个指标的变量,这两个指标就会如同真空环境下物体的运动,只会按照既有的规律客观的运动下去。 真正的变量是人的两个指标——第1个指标和第3个指标。 满清王朝无法完成中国工业化的缘由,即在于满洲本位制,让第3个指标所考察的对象无法爆发出强大的执行力。自然,第1个指标也无从谈起,满洲本位制下,有心决意推行工业化的儒家士大夫根本掌握不了真正的实权,无法主宰国家大权强力推进工业化。因此,与第1个、第3个指标并建的第2个和第4个指标也就无法爆发出应有的工业化进程。 归根结底的说,中国落后与中国文明没有丝毫关系,不论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都不能支持中国近代不能工业化或者工业化过慢的逻辑。唯一能够解释的缘由,只能是满清王朝作为部族王朝根深蒂固的满洲本位制,防汉制汉,严重制约了满清王朝在人的方面的两个指标,导致中国近代工业化速度过慢,相对性的与西方差距越来越大。 联邦制宪政政体也不是行政机关的权力受掣肘吧,准确得说应该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前没有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在行政上属于平级机构。行政平级机构之间,当然不能互相发行政指令了。 如果联邦政府非要向各地推广一些行政政策只能设一些特区,先在特区实验,取得实际效果后再各州推广,比如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 这个政体框架上,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还是属于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这个结构一旦定型,很难有变化。 中国民间要想出现对经济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大资本可能性也很小,对大资本进行行政性征收这种做法也不妥。 如果国家公权力要作这类干预,也应该依据法律而不是行政权。按五个委会员的设置,类似设五个分管项目不同的宪法法院。那作出这类干预民间资本的裁定也应该由财政经济委员会作出,属于违宪审查裁定的性质。 财政经济委员会除了对政府的财政经济预算规划作维持和不维持的裁定外,如果对民间资本在重大经济危机时的责任作出制裁,权力要加强,这个类似以前美联储的格林斯潘角色,不过格林斯潘是一个人,委员会是十六个人。格林斯潘的“独裁”权仅限于调节利率,而这个委员会这方面权力要加强,有哪些权限范围,怎么提请启动,这些程序都要作一些设置。 (责任编辑:百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