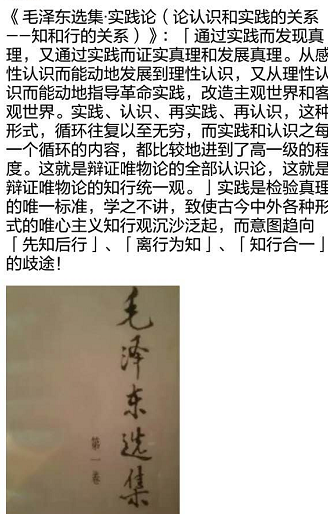 “未尝离行以为知”是王夫之知行观的灵魂,他对知行关系的所有看法都以这一点为基础、前提或由此推导出来。在王夫之的知行观中,“未尝离行以为知”使行是知行关系的根本方面成为必然结论,同时是理解知行辩证统一、知反作用于行的理论前提。换言之,无论是知行的辩证统一,还是知反作用于行都是以承认、肯定“未尝离行以为知”为理论前提的。对于他的知行观而言,有了“未尝离行以为知”这一本体论上的行先知后,才可能更深刻地理解知行如何相依以及知指导行的真正含义。此外,行之“兼知”、“统知”和知的目的是行、行是检验知的标准等是“未尝离行以为知”的延伸或推演结果。与此相关,只有从“未尝离行以为知”入手,才能将王夫之所讲的知行相互依赖、知指导行与朱熹、王守仁的看法区分开来。这一切表明,只有牢记、把握“未尝离行以为知”,才能领略王夫之知行观的精神主旨和价值所归。 首先,王夫之的知行观以行为本,扭转了理学以知为本的思想倾向。在反思、审视理学知行观的过程中,王夫之得出的结论是:理学知行观的共同失误和致命缺陷是以知废行。基于这一结论,他提出了纠正方案――“未尝离行以为知”,以此强调知源于行,用以行为本代替理学的以知为本,使行成为知行关系的决定因素和根本方面。 王夫之不认同朱熹和王守仁的知行观。对此,他分析说,朱熹知行观的核心命题是知先行后,这一观点“立一划然之次序,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意思是说,朱熹的错误在于强调先知后行,由于知无止境而最后抛弃行――“先知以废行”,“先知后行,划然离行以为知者也。”(《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王守仁知行观的核心命题――“知行合一”违反常识,是“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意思是说,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行,而是天赋良知或主观意识活动,其错误在于“以知代行”乃至“销行以归知”――以知吞并了行,从而取消了行。 在分别指出了朱熹、王守仁知行观的致命缺陷之后,王夫之进一步总结并揭露说,两人对知行关系的主张表面看来截然对立,其实质却完全相同――以知为本、以知废行。这表明,在对知行关系的认定上,朱熹和王守仁“异尚而同归”。依据王夫之的分析和鉴定,理学知行观的共同错误是崇尚知而排斥、取消行,否认知对行的依赖性,从而抹杀了行在知行关系中的首要地位。应该看到,王夫之对朱熹、王守仁的评价虽然是站在另一种立场和角度进行的,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理学知行观的共同本质――重知。这一结论是客观的,这一点在理学家们对以知为先、为本的不遗余力、不厌其烦且不约而同的呼吁中得到了证明。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基于对理学知行观的这种认定,与理学家对知的偏袒针锋相对,王夫之强调“未尝离行以为知”,将行视为知行关系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方面,以此建构了与理学家的以知为先、为本迥异其趣的知行观。 其次,将知行由理学侧重的伦理、道德领域扩展到认识领域。王夫之对知、行内涵的界定和对知行关系的阐释具有迥异于理学的维度和立场――无论对知、行内涵的界定还是对知行关系的阐释都不是从伦理、道德角度立论的,致使知、行以及知行关系都不再侧重道德领域。进而言之,王夫之所讲的知、行及知行关系之所以不再限于道德领域,既与他对知、行的界定息息相通,也与其对“未尝离行以为知”的强调密切相关。 受制于“未尝离行以为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王夫之所讲的知指人通过行获得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即格物、致知;行主要指个人“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的“应事接物”(《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的活动,即为、习、履、实践等。在这里,他没有完全排除知、行的道德内涵和知行关系的伦理维度,然而,这些已不再是知、行的主要内涵或知行关系的基本维度,更不是唯一维度。对王夫之的思想进行全面考察可以发现,其知行观的重心在实践领域,尤其是认识领域,正是对认识领域的侧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尝离行以为知”。 进而言之,由于不再将知、行限于道德领域,王夫之的知行观具有不同于理学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侧重。这在突出早期启蒙思想家不同于理学家的价值旨趣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早期启蒙思想与理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体系,不像理学那样是道德哲学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知行关系的立论视角和维度的转变使行有了不知而行的可能性。在知、行不再局限于道德领域的前提下,格物、致知变成了认识或实践活动,不再像理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道德体悟、道德观念或道德实践。格物、致知内涵的变革为早期启蒙思想不再是道德哲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有力证据。 (责任编辑:相天) |
